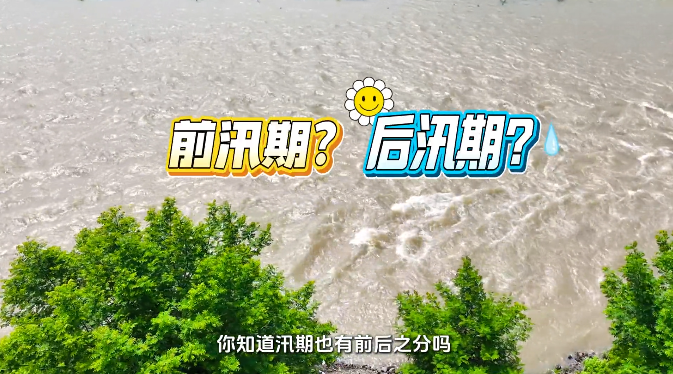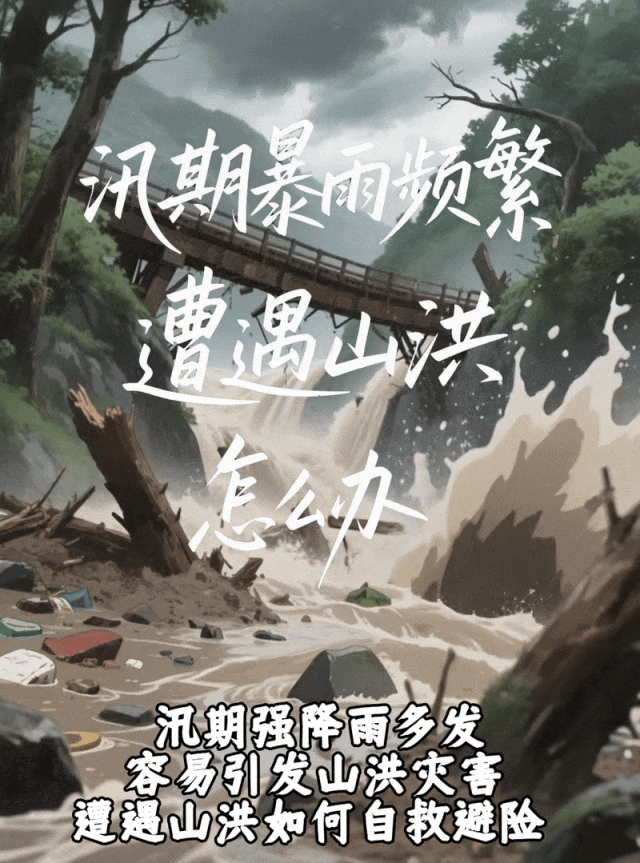“火命”東坡治水記
□王乃岳
林語堂在《蘇東坡傳》里評價蘇東坡是火命,并給出了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他一生都精力旺盛,他的氣質和生活猶如跳動飛舞的火焰,處處給人以生命的溫暖;二是因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處,不是憂愁全城鎮的用水,就是擔心運河和水井的開鑿。縱觀蘇軾一生,主業是做官,盛名于詩文書畫,畢其一生都在治水。本文以孔凡禮先生編撰的《蘇軾年譜》中宋人記載的文獻為依據,以蘇軾在地方任職經歷為脈絡,梳理其治水的印跡與業績,力求完整、力求于史有據。
鳳翔(1061—1064年):首度出仕 抗旱求雨革新河運
蘇軾在地方出仕的首職為鳳翔府判官,相當于地方州府的秘書長。赴任后正值鳳翔連續干旱,蘇軾受命禱雨,先后兩次專程到太白山等地禱雨。這期間,他撰寫了《禱龍水祝文》等多篇禱雨文,禱雨成功后還興奮地將自己官邸修建的亭子命名為“喜雨亭”,寫下了著名的《喜雨亭記》。
修河運衙規。蘇軾了解到當地百姓背負著“黃河船夫”的特殊徭役,每年都要在終南山砍伐木材編成木筏,裝載著來自西北各地的官方物資,沿著渭河進入黃河最終運抵東京。河運要經過三門峽等險峻之地,在汛期可謂九死一生,蘇軾調查發現很多公物明明無須緊急運送,當地部分官員卻毫無悲憫之心,仍強迫服役的百姓趕在黃河汛期出發,導致“衙前以破產者相繼”。蘇軾抓住問題要害,果斷修改了制度規定,讓服役的百姓可以自己選擇運輸時間,不由官府統一規定,不僅降低了運費,還可避開黃河汛期風險,使徭役的危害減少了一半。
命名東湖。清道光年間,鳳翔知府白維清的《重修東湖碑記》記載,蘇軾在鳳翔為官時倡導官民疏浚擴池,引城西北鳳凰泉水注入東湖,兼顧排澇與灌溉的功能。因此事沒有宋代的文字記載,一定程度存疑。但蘇軾在鳳翔為官時所作《東湖》一詩盛贊東湖美景,是鳳翔東湖最早的歌詠,飲鳳池改名東湖很有可能是源于蘇軾。
杭州(1071—1074年、1089—1092年):兩度為官 開湖浚河修堤賑災
1071年,蘇軾任杭州通判,為知州副職,類似于紀委書記兼中央特派員。1089年,任杭州知州,是地方州府的主要負責人。兩度杭州任官,蘇軾同白居易一樣最顯著政績集中于治水。
修浚錢塘六井。蘇軾任通判時,走訪民間疾苦,發現杭州百姓最關心期盼的就是解決用水難的問題,“知水苦惡,惟負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蘇軾配合太守陳襄組織人員不到一年完成了對錢塘六井的修復治理工程。蘇軾親筆撰寫了《錢塘六井記》,詳細記敘了六井的修復過程和具體工程措施。
賑濟旱災。蘇軾任杭州通判時,常州、蘇州等地大旱,他奉命用7個多月的時間賑災救濟饑民。因一路目睹饑民的悲歌哀號,他在除夕夜住在常州船上,不忍上岸打擾百姓,在一盞孤燈下守歲。在賑災過程中,他寫下《無錫道中賦水車》等記載民間旱災疾苦、痛斥官吏隱瞞災情、不顧百姓死活行為的詩歌。蘇軾在完成賑災任務后思考良久,撰寫了《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詳細向朝廷匯報了對旱災、蝗災的實地考察結果,對官吏隱瞞災情的質疑,對災民的同情,以及對朝廷減免稅賦的建議。蘇軾還針對水旱和臺風災情奏請了多篇浙西災傷書。在任杭州通判期間,他還受轉運司差遣,赴湖州“相度堤岸利害”,檢查湖州的堤防建設;他還在杭州接受過朝廷派遣、由沈括帶隊的農田水利專項檢查。應該說,這些經歷都豐富了他的治水閱歷及見解。
乞開西湖修建蘇堤。1089年,蘇軾重返杭州任知州,他發現當年修復的六井幾近荒廢,因為水草泥沙淤塞和圍湖墾田導致西湖湖面只剩一半。蘇軾一周內接連向朝廷上報了《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陳述“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這兩篇報告集中展現了蘇軾作為官員、文學家、工程師的氣質與風范。第一篇報告是寫給皇帝的,1600字,言簡意賅,站位高、目的明,以情動人;第二篇是寫給三省的,3600字,系統全面,措施實、支撐足,以理服人。在寫給皇帝的報告中,開宗明義論述了治水關系國運與民心向背,圣人要順應民心興利除害,闡述“西湖有不可廢者五”,5條理由分別是生態、人飲、灌溉、河運、經濟。第一條西湖的放生祈福現在是生態問題,但在當時主要是為皇帝祈福,是妥妥的“政治第一”,體現了對皇帝的尊敬,緊接著一氣呵成論述人飲、灌溉、河運主要水利功能,最后又用釀酒課稅等經濟價值予以收尾。在給皇帝的報告中,不僅對總體工程量、用工總數定量進行表述,還重點闡述了經費來源,考慮到朝廷財政困難,蘇軾創新投融資路徑,提出了特殊的政策扶持,申請一百“度牒”(當時官府發給出家和尚或道士的免除徭役、受到依法保護的憑證,價值昂貴,可用來換錢、換米的硬通貨)予以扶持。在給三省寫的報告中,蘇軾在開篇闡述民間疾苦,翔實描述了百姓和基層官員的訴求,在充分調研論證的基礎上,歸結為請求上級批準的6條建議,不僅有各項工程的選址、施工技術、土方量、用工量等具體建設細節,還充分考慮了工程建設和建成后的管理措施。如提出招募災民“以工代賑”;在縣衙門組建“開湖司”專門負責對西湖的管理維護;設三塔為界碑明確湖面禁植范圍(今“三潭映月”);在湖邊招租農民種植菱角并兼顧清除水草,租金補充工程維護資金,等等。河湖管理、生態補償理念的輪廓清晰可見。在得到朝廷同意治理的批復之后,蘇軾動員20萬民工疏浚西湖,并用挖出來的水草和淤泥,堆筑起橫貫湖面的長堤,在堤上修橋、種樹形成今日之“蘇堤”。
整治水道疏浚運河。蘇軾任杭州通判時就深知“父老皆云:‘惟苦運河淤塞’”。在任知州后,他進行了詳細規劃,懇請年老的水利專家出山建設,并撰寫《乞子珪師號狀》為建設者申請獎勵。當時,流經杭州城區的鹽橋河和流經郊區的茅山河是杭州城內兩條水運干道,分別與大運河及錢塘江相連。由于錢塘江江潮倒灌,所挾泥沙導致兩條運河淤積,每隔幾年就要疏浚,勞民傷財。蘇軾在錢塘江與城區運河交匯處修筑水閘確保江潮不倒灌,讓錢塘江潮先入郊區運河,待潮平沙沉后再放清水入城區運河,既保證城區運河不被淤積,又保證這條主運道有足夠水量通江達海。同時,他用很小的成本對郊區運河定期挖沙疏浚,建閘讓城區運河又連接西湖水,使得“江潮不復入市”,河道無淤積之虞。在整治好兩條運河后,蘇軾勘測錢塘江并上奏《乞相度開石門河狀》,籌劃開鑿連通錢塘江的石門運河,遺憾的是他很快離任未能實現。
密州(1074—1076年):首次主政 祈雨修井賑災
1074年,蘇軾在杭州通判任上期滿,升任密州知州,這是他首次主政一方。針對密州連年大旱的現狀,他在寫給皇帝的《密州謝上表》,陳奏懇請豁免百姓的秋糧賦稅。為應對旱災引發的蝗災,他向農民學習經驗,身先士卒,指揮捕蝗救災,并開倉賑災,動用官米獎勵捕蝗人。由于連年干旱饑荒,產生了大量棄嬰,蘇軾下令州府官員到野外去撿拾棄嬰,并將棄嬰安排給沒有子女的家庭撫養,州府按月發放粟米6斗,從而挽救了不少生命。10年后蘇軾在赴任登州途中經過密州,見到當年他救助的嬰兒皆已長大為少年,他欣喜感慨“當時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顏”。
雙管齊下治旱。“工程措施”主要是開源與攔蓄,蘇軾在常山附近發現好的水源后“乃琢石為井”,命名為雩泉,并作《雩泉記》。他修的雩泉井和井亭至今還在,仍為當地居民提供生活用水。蘇軾在密州所作《滿江紅·東武會流杯亭》寫道:“東武南城,新堤固、漣漪初溢”“其下有堤,壅邞淇水入城。”可見當時他應該是新修了堤防,引邞淇河水入城,并有在此修壩大規模引水的規劃。此事可從10年后他途經密州作《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奉勸現任太守繼續興修水壩中管窺一二。至于“非工程措施”,蘇軾做得最多的就是求雨,從文獻記載來看,兩年間他至少5次到常山禱雨并作祝文,且非常靈驗。有一次,他求雨當晚就下了大雨,他不僅撰寫了《次韻章傳道喜雨》等詩文,還重修常山廟、封常山神為侯。
徐州(1077—1079年):抗洪立奇功 黃樓湮風雨
抵御黃河洪水。蘇軾徐州到任后不到3個月,黃河在今濮陽段決口,奪泗入淮、洶涌南下抵達徐州城。徐州三面被淹,城外水位比城內平地高出一丈九寸(約合今2.5米),徐州成了一座孤城和水下城。蘇軾在危急關頭盡顯擔當與謀略,于洪水來臨前準備好土石草料等抗洪物資、組織城中百姓加固城墻“外發長楗”。危急時刻,他涉水趕到徐州禁軍駐地(按當時律令,州官無權調動禁軍)懇請禁軍官兵幫助抗洪。禁軍首領深受感動:“太守猶不避涂潦,吾儕小人,當效命!”有了禁軍支持,蘇軾緊急修筑近千丈的東南長堤,長堤修成當日洪水就奔涌而來,奇跡般地再次將洪水拒之城外。他還“使官吏分堵以守”,分段明確防汛責任,并組織官吏給城內躲在高處避險的百姓送糧食以防餓斃。面對準備逃亡的富人,蘇軾力斥:“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在禁止富人外逃的同時,蘇軾鏗鏘高呼:“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他夙夜不怠,“廬于城上,過家門而不入”,住在城墻上的帳篷里誓與城池共存亡,讓全城百姓吃下定心丸。嚴防死守70多天后,洪水終于退卻。取得抗洪勝利后,蘇軾受到了皇帝嘉獎,并刻詔書于石碑,這是蘇軾地方任官時的最高榮譽。蘇軾將這次抗洪和受表彰的經過記為《獎諭敕記》《熙寧防河錄》,在得知黃河部分支流回復故道后喜作《河復》詩 。
建木岸修黃樓。洪水退后,蘇軾馬上開展災后重建,他連續上帖請求朝廷免去徐州百姓賦稅,并請求撥款修建石岸(堤),保全防洪長久之利。奏請石岸不遂后重新申請費用減半的堅木加固堤防。得到批準后,他帶領百姓“增筑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蘇軾一直憂心黃河決口未塞和堤防修復問題,多次與友人在詩簡中提及,在《答呂梁仲屯田》詩文中記錄了這場洪水造成的危害,鼓勵同事堅定筑城固堤的決心。在洪水次年春,旱澇急轉,大旱時他又作《徐州祈雨青詞》等多首禱雨、謝雨詩詞。為紀念戰勝黃河水患,蘇軾命人在城東門建造了一座兩層高樓,并用五行“土實勝水”的黃土顏色飾以外觀,命名為黃樓,由蘇轍撰寫《黃樓賦》記敘蘇軾徐州抗洪功績與修樓經過。蘇軾元祐黨禍被迫害后黃樓更名,《黃樓賦》碑石被毀,在黃河南岸的原址如今已湮沒在歷史的風雨中。
湖州(1079年)、登州(1085年):彈指間仍操勞治水
1079年,蘇軾自徐州改任湖州知州只有3個月就因“烏臺詩案”被捕。1085年,他到任登州知州僅僅5天便接到還朝的調令。即便時光短暫,蘇軾仍在兩地留下了治水印跡。
在湖州時,久雨不晴,蘇軾曾在黃龍洞祈望天晴,并作詩刻于石壁上。他在湖州峴山寺修筑堤防,后人命名為“蘇堤”。在登州時,他關注海神廟的遷建,幸運看到海市蜃樓,寫下七言詩《登州海市》。
潁州(1091—1092年)、揚州(1092年)、定州(1093—1094年):兩年閱三州 治湖廢溝修漕規
1091年,蘇軾自杭州回朝任官,3年間反復在朝廷與地方州府調動頻繁,先后到潁州、揚州、定州任職。蘇軾不禁發出了“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的感嘆。雖然在三州任職的時間都在半年左右,但他仍做了大量的治水工作。
拒開八丈溝。蘇軾到任潁州時,當地運籌多年的重大水利工程八丈溝即將開工,擬新修的八丈溝長達300多里,旨在疏導積水消水患。但蘇軾通過實地勘察發現重大隱患,不惜得罪朝廷和都水監及其他地方官員,堅決反對興建八丈溝,不做“太平官”。因八丈溝工程已得到朝廷批準、多段準備工程已經開工,拒開風險極大。蘇軾連上《申省論八丈溝利害狀》《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等3道奏折,他派員系統測量淮河、潁河水文與高程,得出八丈溝入淮水位在淮河泛漲時高于上游水位八尺五寸(2.83米),修成后淮水勢必倒灌的結論。如若開挖八丈溝,不僅勞民傷財,解除不了水患,還會使潁州成為汪洋。因其論證嚴謹翔實、情理并茂,最終朝廷采信了蘇軾建議停挖八丈溝,為潁州免除了大量夫役和錢米。
新開西湖。蘇軾在潁州奏請留下開挖黃河的民夫萬余人,集中力量開挖潁州的溝渠。他在完成溝渠整治任務后,又趁熱打鐵,“千夫余力起三閘”,浚治潁州西湖。雖然目前缺少治理潁州西湖的史志記載,但從蘇軾與友人的書簡、詩歌中仍能清晰展現出工程的規劃、建設過程。可惜西湖治理工程尚未完工,蘇軾就被調往了揚州。次年工程完工后,蘇軾作詩“大千起滅一塵里,未覺杭潁誰雌雄”,他將治理潁州、杭州西湖并列為自己的驕傲。蘇軾在潁州還疏浚護城河盤活水系,祈雨雪作《書潁州禱雨詩歌》等多篇詩文。他還多次上書反映潁州災情祈求賑災,撰寫《奏淮南閉糴狀》控訴其他州府地方保護,不讓潁州災民過淮河買稻米、稻種的問題。
寬稅改漕規。蘇軾在揚州替飽受水旱災害的百姓請愿,撰寫《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建議朝廷寬免百姓兇年所欠官稅,最終朝廷下詔寬免1年。針對沿河稅務機構嚴查過往漕船、對私貨征收過稅的問題,蘇軾呈上《乞歲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等奏折批評盤檢漕船之弊,認為此舉不僅影響漕運效率,還逼迫運工因無法生計而盜竊漕糧,建議允許運工利用漕船運銷私貨獲利。朝廷采納了蘇軾的建議,啟用新規,既促進了通船效率、商品流通,又有效地提升了運工的積極性。
賑濟軍民。1093年,蘇軾以雙學士、禮部尚書的身份兼知定州,地位為他任地方官時最高的。但半年后被貶,定州成為他仕途最后一個和落差最大的拐點。定州當時是宋遼對峙的極邊軍事要地,蘇軾到任時面臨水災糧匱、士兵逃亡、百姓饑饉的局面,他北岳祈雨奏旱情,撰寫《乞將損弱米貸與上戶令賑濟佃客狀》等奏折,請求減價賣米平抑糧價,進而申請將倉中陳糧貸給百姓,待農戶豐年再償還,并以好米補充軍糧。他的建議被采納,有效化解了極易引發的水災饑民突變。
黃州(1080—1084年)、惠州(1094—1097年)、儋州(1097—1100年):貶謫之地心系治水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即使在遭貶謫之地沒有參與公事的權利下,但仍利用他的影響力推動治水。蘇軾遭貶謫黃州時,官職為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水部員外郎是主管水利相關事務的官員,當時加掛在蘇軾身上屬于加官虛銜、寄祿官階,但結合他終生治水的“平生功業”倒也合適。
推廣水力農具。蘇軾遭貶謫黃州時,發現當地農民用“秧馬”在水田里插秧高效快捷,此后他一直推廣這一先進農具。他在惠州編寫多部秧馬歌謠,教授秧馬制作、使用之法,連同水力碓磨一同推薦給博羅縣令。很快,這些中原的先進農具“今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
建惠州兩橋一堤。針對惠州四面環水、百姓出入不便的問題,蘇軾充分吸取當地人意見,與惠州太守詹范、廣南東路提刑程之才商議興建東新橋、西新橋。蘇軾親自參與工程規劃,還點名推薦水利專家牽頭建設“其工必堅久”。在工程經費不足時,蘇軾先捐了皇帝賞賜自己的犀帶,又求助弟弟蘇轍將得賜的數千兩黃金捐了出來。西新橋修建時還建了連接橋岸的堤防,后人亦稱“蘇公堤”。
引水廣州。廣州太守王敏仲因“一城人好飲咸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向遭貶謫惠州的蘇軾請教破解之法。蘇軾回信建議,將離廣州20里的蒲澗山之水通過竹管引入城中,蘇軾就工程的選址路線、建設工藝、經費預算、后續維護工作都做了詳盡闡述,并推薦水利專家牽頭建設。王敏仲聽從蘇軾的建議予以興建,使廣州百姓喝上“自來水”。
鑿井海南。蘇軾被貶往儋州途中路過瓊州,發現當地百姓飲水困難,便觀察地形在城東北角尋得雙泉,并指鑿浮粟泉、洗心泉成井。待3年后他北歸再次途經瓊州時,應當地官員邀請為泉邊亭臺題名作詩為“泂酌”。他在儋州發現當地的井水因濱海而味咸,在天慶觀中發現一孔色白如乳的甘泉,將泉開鑿后稱為“乳泉”,并寫下《天慶觀乳泉賦》。
廟堂之高:一心謀劃治水良策
蘇軾在朝廷任職時位處核心層,還曾做過帝師,大多為議政監督、決策咨詢等工作。在朝期間,他對治水戰略、科技、改革措施提出過大量有見地的見解。
主張黃河北流。北宋的黃河河道變遷劇烈,水患災害大大超越前代。1034年,黃河在濮陽決口自東流改為北流后,由此引發治河爭論長達70年。主張恢復東流的王安石、文彥博、司馬光傾向人工導河恢復東流,達到恢復淹沒良田、軍事防備契丹的目的。主張保持北流的歐陽修、蘇轍、蘇軾傾向于河流自然規律不可違、民力凋敝,不可再導河勞民傷財。東流派3次贏得爭論勝利,但3次人工回河東流先后失敗,都以黃河復歸北流而告終。蘇軾任帝師在給年幼的宋哲宗授課時,“超綱”奏述了批判東流的意見,遭到當權的東流派大臣惱怒彈劾,間接導致他離職請辭赴地方任職。蘇軾晚年在儋州聽聞多年后黃河最終仍恢復北流,感慨“今斯言乃驗”,作詩“三策已應思賈讓,孤忠終未赦虞翻”。
建言太湖治理。蘇軾任翰林學士、吏部尚書時非常認同單鍔提出的根治太湖水患的規劃和措施。他專門向皇帝奏《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并親自為此狀附言,認為單鍔精通水利學問,撰寫的《吳中水利書》非常值得推廣應用,懇請將他的建議和單鍔的書下發,委派能干且了解水利的官吏,核實這些建議和措施是否可行后,報送朝廷,對太湖水患予以治理。可惜蘇軾的建議未被重視。
建言《農田水利法》。《農田水利法》是王安石改革的重要法令。雖然蘇軾與王安石在政見上分歧較大,但對其興修水利、開墾荒田等政令,蘇軾并沒有否定,他只是對某些具體做法表示擔憂并提出建議。在《上神宗皇帝書》中,他對施行農田水利政令提出3點意見,涉及灌溉方式、古陂廢堰產權等方面,特別是,他認為朝廷鼓勵官私興辦農田水利要賞罰嚴明,“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會使那些“妄庸輕剽,浮浪奸人”也“爭言水利”;對“妄有申陳”“誤興工役”者必須懲處。
“東坡熱”現象經久不衰,已經成為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蘇軾胸懷浩然正氣,無論廟堂之上還是江湖之遠永不懈怠、為民操勞,從不以黨派和私念出發分析利弊;他性情樂觀豁達,愿意與不同層級的人交際,對世界始終抱有溫和的同情心,對未知事物始終抱有探索的進取心;他文如萬斛泉源、行如跳躍火焰,復合人生所產生的跨界能力令人欽佩。
“一百個人眼中有一百個蘇東坡”,他曾是寒窗苦讀的小鎮做題家,他曾是愛妻思弟的有情郎,他曾是官場職場的受氣包,他曾是萬人景仰的大明星。在我們水利工作者眼里,他更是治水管水的六邊形戰士,是妥妥的被做官和文學才華“耽誤”的水利達人。
來源:中國水利網站 2025年8月11日
作者:王乃岳
責任編輯:王瑜